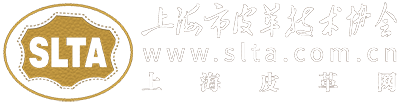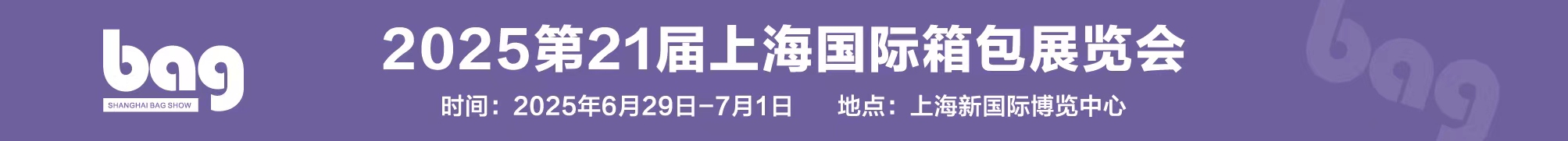【皮革名士】徐明骥——启示来自昔日的辉煌之后
温:成都被誉为“天府之国”,也是中国皮革人才的摇篮。成都制革厂在20世纪中期是我国久负盛名的皮革大厂,请问当年成革厂的盛况如何? 徐:成都制革厂是当年国内一家规模不小的综合性工厂。其主要产品除制革、皮鞋两大块外,还有少量军工配件、牛胶、服装等产品,无论是军需还是民用,尚有点知名度。 这个厂的发展大致可分3个阶段时期: (1)1950—1957年:新中国成立初,民用加军需。产品原以山羊鞋面革为主,1950年因西南后勤需要军用靴鞋供应,遂开始生产外底革、鞋面革和士兵鞋。 (2)1958—1975年:这个时期主要两大任务:一是建新厂,二是军转民。新建制革厂的主体包括制革和制鞋两个部分;在产品方向“军转民”的大背景下,调整产品结构主要体现为从牛皮制革转向猪皮制革。 (3)1975年以后时期。值得一提的是为满足当时市场需求,大家努力试制,一时新产品层出不穷,猪草、牛草、羊革,几乎全面开花,成革厂也兴旺外盛。 温:徐老,当时的西南总后军需生产是个什么概念?成都制革厂的具体任务是什么? 徐:当时的西南总后军需生产的产品,主要是军用服装和军用靴鞋。成都制革厂当时的具体任务是生产外底革、鞋面革和士兵鞋,这就包括制革和皮鞋两块。因为生产军用靴鞋要求使用真皮的面、底料,我们就得自行生产底革和鞋面革,直接供应制作士兵鞋。从技术要求而言,底革要求坚实耐磨,鞋面革则要求是黄牛多脂鞋面革。 温:请问你们当时在生产外底革和鞋面革的过程中,曾经遇到过哪些技术难关?是如何化解克服的? 徐:当时生产底革的关键问题是植物鞣剂(栲胶)的优选和供应有困难,市场上能供应的量极小。经探索后,我们采用低温浸提工艺,解决了青杠椀(子)鞣剂滲透慢、沉淀多、颜色深等缺点,运用长周期鞣制出品质优良的底革。经实际穿用试验,坚实耐磨,被评全军第一。技术亮点是如果没提条件控制适当,青杠椀(子)可作为优良鞣剂。可惜,限于条件,没有机会深入研究。至于鞋面革,是生产军用靴鞋的需要,上级要求生产黄牛多脂鞋面革。于是,我们参考前苏联的重鉻重植工艺,试制相当成功,既满足当时的军需生产,又为后来制造各种铬植结合鞣革(如装具革、凉席革)提供了参考范例。
励精图治 率领一班人马创建新厂 温:您当年在成都制革总厂任技术厂长兼总工程师时,身居要职,您觉得这个“舞台”对于施展您的才华是否得心应手? 徐:那是1956年,我被调到西南军需生产管理局着手建新厂,雷厉风行,从规划设计,基本建设,设备安装到调试投产,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,一气呵成,如期完成任务,未曾发生重大偏差,确保 1958年全面投入生产。我自1957年任成革厂的技术副厂长兼总工程师,一直到1983年届满60岁才被免去行政职务。怎么说呢?其间前后长达26年,实际工作重心多次乃至于经常变动,时而忙于技术工作,时而应对行政事务。不过还算好,实际上始终未脱离技术工作。当然,随着工厂规模的不断扩大,管理层次增多,的确有些被架空的倾向。 温:徐老,请问您当时是怎样实施技术管理和应对日常要务的? 徐:从总体上来看,前后35年间,技术工作进展还算比较顺利,究其原因,除了党委一直重视技术工作外,其关键在于“三个配套”;即运营机构的配套,管理机制的配套和技术人员的配套。 温:能否请您解读一下这“三个配套”,或者说这“三个配套”是怎么回事? 徐:首先是运营机构的配套。成革厂始终坚持生产与科研两套机构并驾齐驱的管理模式。尤其是试验室,几十年一直坚持,不受干扰,并不断完善试验设施与手段。 其次是管理机制的配套。 技术管理系统的基本架构包括:技术副厂长兼总工程师负责制,下属厂部技术(部、科),分厂和车间技术(股、组)、产品工程师(室)、实验室、工段、班组技术员、技师,熟练操作技工等。逐级成链,交错成网,各司其职,又相辅相成。同时,总工兼有技术厂长的职权是项重要的机制,这可避免管理上的某些扯皮,也易于将科研和技术纳入企业的总体计划,并利于落实必要的人、财、物投人的及时按计划到位,以保障技术措施的顺利实施。当然,担当这个角色的人,首先应该是总工,然后,才是厂长,这一点很重要,我有切身体会。 技术人员的配套,包含两层意思:一为人员层次结构上的配套。即我们不但关注、引导有学历、有经验、能独当一面的工程师,也注意培育、造就有实际经验的技术员和技师,而且更注重锻炼有特殊专长的技术工人。我们的技术人员为数不少,最多时可达百人,是一支训练有素、门类较全、能独立作战的队伍。所以,全厂技术目标与计划任务的实现,主要依靠他们的骨干作用。我作为技术主管,除了贯彻厂部任务、编制技术计划、制订实施方案外,主要是坐镇点将、检查督导、现场协调和临阵排难。
运筹帷幄 指挥技术团队开发新品 温:在产品“军转民”的背景下,新厂所面临的产品结构大调整是势在必行的,那么,技术系统将首当其冲,请您谈谈当时是如何应对的?有何亮点? 徐:调整产品结构主要体现为从牛皮转向猪皮制革。当时,正值轻工业部根据中国国情号召大力推行猪皮制革,并在全国范围开展美化猪革的研究和宣传工作。西南地区闻风而动,我们厂也试验了不少品种,但真正能大批量生产的几乎只有猪修正面革,而且直到使用了上海生产的丙烯酸树脂后,质量才得以过关。后来,成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主要品种。该项成果与工艺通过四川省皮革学会组织的技术交流活动,在省内得到推广。 温:一个成功的技术团队,除了有一位知人善任、多谋善断、富有凝聚力的好统领和一批能相互理解、共同协作,富有敢想、敢干、敢作、敢为的人外,我想,这个团队背后的坚强支柱与后盾也是至关重要的,您说呢? 徐:在成都制革厂这一班人中,首先要提到的是1950年军需部派来的军事代表,后来任厂党委书记的杨阜同志。当年,正是他顶着“包庇”、重用资产阶级旧知识分子的政治压力(这也是他在历次运动中被蒙受的主要“罪名”),放手让我们大胆工作,而且,有了责任他承担,有了成绩归功于大家。这样的坚强领导是难能可贵的,也为以后顺利开展技术工作打下扎实的政治基础。 温:您作为这支技术团队的“统帅”,那么所拥有的一班“大将”呢?可否请您谈谈您最默契的合作者或得力助手是何人? 徐:在专业技术方面的长期合作者有:沈瑞麟、叶式烈二位高级工程师。他们一直负责有关科研、开发、试制方面的工作。当时,每年都有不少新产品、新工艺的成果,转化为生产力的比例也许比专业研究单位还要高一些。另外,还有曾繁静、孟怀纪二位工程师。她(他)们专职负责解决日常生产技术的运行管理和试验成果的转化工作。曾工在开发山羊服装革与培训技术工人等方面颇有建树,功不可没;孟工在开发猪革品种和提高猪绒面革质量方面有突出成就,贡献卓著。 温:徐老,您们的技术团队就像一支庞大的交响乐团,您是这支乐团的指挥,您的作用不可低估。恕我出难题,可否请您对自己说点什么? 徐:我一开头就说了,败军之将,不足以言勇嘛!至于这支技术团队,当时在业内确属不可多得,成都制革厂当年兴旺鼎盛,新品种百花齐放,他们做出了巨大贡献,功不可没;他们的奉献精神,可歌可泣!至于我个人,只是做了一些分内事,一些组织协调工作。总之,个人的作为微不足道。
【人物传略-后记】
相关新闻
-
2024-07-05
【皮革名士】:《中国皮革名士访谈录》精选报道专栏——开篇启航
-
2024-10-24
【皮革名士】王全杰教授,一位皮革科技界出类拔萃的风云人物
-
2024-10-24
【皮革名士】麻国栋——躬耕皮革四十年,非梦亦非烟
-
2024-10-24
【皮革名士】刘白玲——春风大雅能容物,秋水文章不染尘
-
2024-10-24
【皮革名士】千里之行始于足下—专访马建中教授